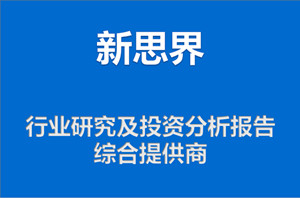沒(méi)有任何一個(gè)人生下來(lái)便無(wú)所不知,所有人都需要從他人身上學(xué)習(xí)到技巧和經(jīng)驗(yàn)。諾貝爾文學(xué)獎(jiǎng)得主艾麗絲·門(mén)羅,因其細(xì)膩且不失犀利的文風(fēng)而廣受贊譽(yù),但關(guān)于這種寫(xiě)作風(fēng)格從何而來(lái),門(mén)羅似乎總是諱莫如深。然而,在一次采訪中,門(mén)羅卻三次提及了一個(gè)人的名字:威廉·麥克斯韋爾。門(mén)羅言下之意,威廉·麥克斯韋爾即便稱不上是她的伯樂(lè)導(dǎo)師,至少也是她的知己師友——某種程度上門(mén)羅成功的寫(xiě)作之路要感激麥克斯韋爾的陪伴。
那么,這位威廉·麥克斯韋爾究竟何許人也,為何能贏得諾獎(jiǎng)得主門(mén)羅如此贊譽(yù)?麥克斯韋爾的本職工作是雜志編輯,他曾就職于美國(guó)著名文藝雜志《紐約客》40載,同時(shí)他還是一位著名的小說(shuō)家、散文家和傳記作者。門(mén)羅正是在麥克斯韋爾任職編輯期間與其相識(shí),在文學(xué)創(chuàng)作方面,兩人堪稱天作之合:門(mén)羅在麥克斯韋爾的幫助指導(dǎo)下越發(fā)成熟,麥克斯韋爾同樣得益于門(mén)羅的鼎力支持。在這種長(zhǎng)期的合作過(guò)程中,門(mén)羅的寫(xiě)作風(fēng)格會(huì)受到麥克斯韋爾的一定影響,也就不足為奇了。
當(dāng)然,門(mén)羅對(duì)麥克斯韋爾的推崇,絕不僅僅因?yàn)閮扇说乃浇灰约昂献髦械南嗷ビ绊憽{溈怂鬼f爾的作品也深得門(mén)羅的認(rèn)可,對(duì)此她從來(lái)不吝嗇溢美之詞。在讀過(guò)威廉·麥克斯韋爾的小說(shuō)《再見(jiàn),明天見(jiàn)》(程應(yīng)鑄譯,南海出版公司)后,門(mén)羅甚至發(fā)出了這樣的感慨:如《百年孤獨(dú)》一樣難以寫(xiě)就,也和它一樣完美,讀完后我恨不能讓時(shí)間倒流,好把自己過(guò)去的作品都重寫(xiě)一遍。天啊,諾獎(jiǎng)得主門(mén)羅竟然要推翻自己?
那么,《再見(jiàn),明天見(jiàn)》一書(shū)又究竟怎樣精彩,能使門(mén)羅甘愿送上至高贊美呢?我們不妨用心品讀。《再見(jiàn),明天見(jiàn)》中的故事發(fā)生在1922年的那個(gè)“未被玷污的美國(guó)”:一聲槍響打破了美國(guó)伊利諾伊州某小鎮(zhèn)的平靜,農(nóng)場(chǎng)佃農(nóng)勞埃德·威爾遜死于非命。不久后,克拉倫斯·史密斯被發(fā)現(xiàn)自殺身亡,而他與威爾遜家的關(guān)系非同一般。隨著調(diào)查的不斷深入,一個(gè)隱藏于兩家人之間的秘密被揭開(kāi)。原來(lái),勞埃德與克拉倫斯本是生死相交的朋友,然而勞埃德竟與克拉倫斯的妻子有染,最終導(dǎo)致克拉倫斯與妻子離婚。摯友的無(wú)義、妻子的無(wú)情、法律的無(wú)力使克拉倫斯深陷絕望,于是他對(duì)昔日老友舉起了罪惡的槍口……
在麥克斯韋爾筆下,兩家人的恩怨情仇錯(cuò)綜復(fù)雜,但絕不雜亂無(wú)章,克拉倫斯內(nèi)心的種種情緒此起彼伏卻又無(wú)比清晰,全書(shū)感傷細(xì)膩的文字亦令人動(dòng)容。不僅如此,故事中還若即若離地隱現(xiàn)作者本人的影子,他以敘述者的角度穿插于故事之中,非但毫無(wú)繁復(fù)累贅之感,反而增加了條理性與真實(shí)感。總之,書(shū)中新穎的故事結(jié)構(gòu)與練達(dá)的敘事方式,讓人不得不感慨這是一個(gè)資深編輯兼著名作家才具備的杰出的寫(xiě)作敘事能力。
“他讓偉大顯得如此容易。”普利策文學(xué)獎(jiǎng)得主理查德·福特對(duì)威廉·麥克斯韋爾及他的《再見(jiàn),明天見(jiàn)》的評(píng)價(jià),可謂一語(yǔ)中的。的確,麥克斯韋爾憑借無(wú)與倫比的寫(xiě)作天賦和穩(wěn)定嫻熟的寫(xiě)作技巧,似乎很輕易地就創(chuàng)作出了一部部經(jīng)典之作,而《再見(jiàn),明天見(jiàn)》一書(shū)則注定成為他不凡寫(xiě)作生涯的偉大注腳。
更多圖書(shū)
讀后感請(qǐng)關(guān)注新思界產(chǎn)業(yè)!